搜索到
1
篇与
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的结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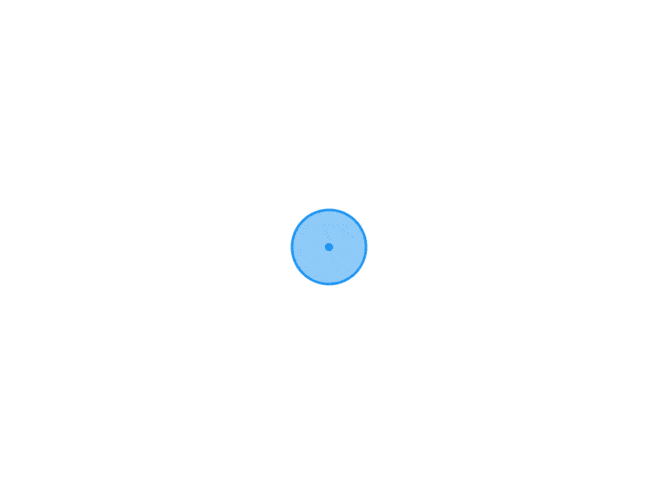 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摘自《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第二章:当代中国启蒙的内在紧张。许纪霖著。 改革在80年代就像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一样,属于神圣词汇,改革具有某种魔力,它承诺所有的社会阶层在改革之中都能获得利益,因而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改革打破了束缚人们多年的传统集权体制,资源集中在国家手里,赋予了全体人民相当的自由创造、发财致富的机会和权利。那时候的改革的核心是放权让利,是一场多边双赢的游戏。大家在改革中,所失去的只是锁链。如果说80年代改革的结果是多边双赢的话,那么90年代的改革就渐渐变化为一场零和游戏。这就发生了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围绕着改革的合法性,90年代发生了两场论战,一场是90年代初的激进与保守的论争,另一场是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前一场论争同样发生在启蒙阵营内部,其核心问题是改革的模式之争。80年代改革的合法性是以革命的名义论证的,改革就是革命,但到90年代,革命的神圣性被消解,引起了对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清算,谁该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失败负责?这样,革命就以激进主义的名义受到了审判,而保守主义又成为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得到了理论上的平反昭雪。激进与保守,背后所预设的,是墨子刻所说的转化与调适的两种对理性的认识论,分别以法国的唯理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为背景。激进与保守论战,最后以保守的大胜而结束,这也预示着自由主义即将脱下各种包装,浮出水面。 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一轮改革,这一轮改革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延续并加快了80年代以来的改革步伐,结果所形成的是从80年代就开始了而到90年代中后期明显定型的三大变化趋势。第一,从政治形态而言,从全能主义的政治转变为善治主义的政治。到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社会的基本确立,中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控制一切的全权主义集权政治,而改变为国家基本放弃了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控制而主控政治领域、在执政理念上照顾和体现民意的善治主义政治。按照康晓光借鉴金耀基提出的概念分析,这一善治主义的政治采取了一种“行政吸纳政治”的治理模式,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尊重和代表精英集团的利益从而获得精英们认同的基础上的。 第二,与此相适应,当代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则从一个总体主义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断裂的社会。按照孙立平的研究,1949年中国所建立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精英的位置不再存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从这一意义上说,总体性社会也是一个“无统治阶级的国家”。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推开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精英阶级。这些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和地方权力精英,虽然人数很少,却控制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成为强势利益集团。精英与一般的民众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资源占有以及与国家沟通能力上,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精英与大众的社会断裂层。这些断裂,不仅发生在精英与大众不同的阶层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同一个阶层内部。断裂,意味着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互相交往的整体,相反的,各个断裂层之间充满了忌恨和隔膜,缺乏最基本的公共信任,从而潜伏着冲突的危机。 第三,改革的游戏规则从打破旧体制的多边双到资源再分配的零和游戏。改革本来是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按照什么样的理念改革,改革对谁有利,成为90年代改革的突出问题。90年代在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精英利益集团,逐渐介入、控制甚至主导了改革的方向和方案,而政府本来应该是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调节者,但在地方政权一级,本身也利益化,与地方的强势精英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关系。而无法介入改革决策的民众,则成为改革的牺牲品。改革的游戏规则从80年代的多边双赢逐渐蜕变为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在所谓的市场竞争、适者生存的理念指导下,造成了一个赢者通吃的局面。一方面是极少数的所谓竞争得胜者,他们垄断了大部分的资源和成果,另一方面是绝大部分的失败者,他们只能得到改革后的残羹冷饭。正如秦晖所分析的,所谓的赢者通吃,在中国不平等的市场规则之中,实质就是权者通吃。 对于改革以来发生的上述变化,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有基本的共识,也对这一现状不满,也一致认为中国除了继续改革,没有任何出路。然而,这些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其根源在何处?又往什么方向改革?按照何种理念?何为改革的优先性原则?在这一系列涉及中国改革和现代性的最基本问题上,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一分歧突出表现在改革的合法性争论上:谁之改革?何种正当性?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就是改革合法性争论的表面化。这场90年代论争的压台戏,涉及范围之广、问题之深刻,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也罕见。这场大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在90年代资本与权力相互渗透和利益高度分化的背景下,什么样的改革具有合法性,因此形成了四个层面的重大分歧:第一是两种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歧,第二是两种民主(宪政民主与全面民主)的分歧,第三是两种公正(交易公正和分配公正)的分歧,最后是关于对现代性的理解上的分歧。而在这些分歧的背后,又涉及80年代启蒙运动中本来已经自明的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民主等一系列基本范畴的重新评价和历史分析,以及对9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这场论战对90年代具有总结的性质,因其在时间上跨世纪,因而对21世纪的中国继续发生着重大影响。 自这场大论战之后,国内外的舆论出现了一种将中国思想界分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大阵营的简单二分法,并权且按照这一二分法为众多知识分子重新站队。应该说,这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二元法是一种具有相当误导性的化约主义,它将中国知识分子对改革的分歧,化约为两种非黑即白的思想倾向。事实上,在当代中国,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其内部都有着相当复杂的区别,特别是在被称为自由主义的阵营中,既有在政治上相当保守而在市场上非常激进的发展至上的经济自由主义,也有注重宪政改革和个人权利的政治自由主义,还有兼顾自由与平等的左翼的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以及其内部的分化,随着论战的深入,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到9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所呈现的,不是对比强烈的两极图景,而是远为丰富而复杂的思想光谱。 如果我们不是分得更细的话,可以说当代中国思想界在改革的问题上,已经分化为五种政治思潮:发展主义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左翼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 发展主义的代表者主要是一批目前在中国经济学界名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渊源主要是里德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发展主义相信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应该来源于企业的制度创新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要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推动产权的私有化改革,解决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发展主义以发展至上为中心,将中国改革定位在企业创新、私有化改革和落实私有产权的合法化这几项经济目标上,至于社会的分配不平等问题,他们认为这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可以等到经济发展以后再来解决。至于政治的自由和民主问题,也被发展主义的发展至上的理念暂时搁置在一边。发展主义到90年代已经体制化,成为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且明显地代表了经济精英的利益和诉求。 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者是一批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坚定的反对者,他们奉哈耶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为自己的理论圭臬,相信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和宪政民主制度,而其前提就是要在法治框架之内,落实包括人身、财产、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内的最基本的人权。他们虽然与发展主义一样赞成私有化,但认为目前的私有化是不公正的,而社会不平等的症结,在于权力远远没有退出市场,是“看得见的脚”干扰了“看不见的手”,唯一解决的途径是全面彻底的市场化,切实落实私人的财产权,将权力完全逐出市场,以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在政治领域,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者坚信,中国目前所有问题,包括腐败和市场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因为政治上缺乏民主宪政和现代法治,特别是缺乏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他们呼吁要在政治改革上着手,全面落实和保障个人的“消极自由”。 新左派是从80年代启蒙运动分离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在国外留过学,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影响。他们将上述的发展主义和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统称为“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为全球资本主义中国化辩护的意识形态。新左派强烈批评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资源再分配中,少数权贵成为最大的得益者,而广大平民成为被剥夺的牺牲品。他们认为这一分配极其不公的国有资产掠夺过程,正是打着“自由经济”、“私有产权”的旗号进行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替少数权贵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提供合法性的借口而已新左派进而指出,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历史中也是一个虚幻的神话,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操控和垄断市场。市场中所谓的机会平等遮蔽了实质的不平等。要实现社会的公正,唯有落实社会经济的民主,让底层民众能够参与经济生活的决策和管理,并在资源分配上向弱势群体倾斜。新左派虽然不反对政治改革,但他们不满意“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消极自由”和“间接民主”,追问是谁之“自由”,何种“民主”。他们批评说,这些表面平等的“消极自由”只是少数权贵能够享受的“自由”,而与广大民众无涉。他们要进一步落实能够保障一般平民广泛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并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保证广大平民享受普遍的生存权和福利权,真正落实自由与民主的基本条件。 左翼自由主义是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他们虽然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与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对新左派虽然有批评,也有部分的同情性了解。在他们看来,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太“右”,而新左派太“左”,对于中国来说,需要超越“左”与“右”的两极,探求一条兼顾自由与公正的“第三条道路”。而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这些欧美的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左翼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他们认为,在中国,不仅需要落实个人的自由,也需要解决社会的公正。他们不像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那样迷信市场,而是认为有好的市场,也会有坏的市场——即权贵资本主义垄断下的市场。在这一被权力扭曲的市场中,哈耶克式的交易公正是不够的,也是很难实现的,必须还有分配的公正,通过国家的制度化力量,在不违背自由的优先性原则之下,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而在政治上,在赞成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同时,又提出公民共和主义和商议性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作为补充,在选举民主之外重视公民文化公民参与和公共领域的公共讨论。 新保守主义思潮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经以新权威主义的形式出现,到90年代中期以后,其善治主义的威权政治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并且也内化到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使得新权威主义不再是一种独立的、有影响的改革思潮。不过,90年代所出现的上述政治模式、社会结构和改革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重提保守主义,这一新的保守主义旨在调和国家、精英和民众的紧张关系,克服出现的社会断裂危机,以建立一个合作主义的国家模式。简单地说,这一合作主义的政治模式,有四项要求:第一,统治集团必须约束自己的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即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权威主义政府;第二,限制经济精英的非法利益,同时完善法治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但要坚决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第三,扩大知识阶级的权利,特别是要保证他们的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第四,保护大众的基本权利,建立法团主义体制和福利国家。 上述这五种改革的思潮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有着或者直接,或者曲折的利益背景,但作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理念,它们更多地体现了超越利益之上的“真理宣称”( truth claims)。承继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知识分子总是将自己看作中国改革的立法者,相信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真理宣称”。而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是异常复杂的,启蒙思想的内在传统也是多元的。启蒙思想内含的众多的价值理念—发展、进步、自由、平等、法治等等,一旦遭遇到复杂的改革处境,就需要启蒙知识分子作出价值性选择:何为自己所理解的最优先的改革原则。而继承了不同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也就在90年代这样一个启蒙后时代里面,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对改革之合法性的论证因而也具有了各有其价值秉承的多元阐释。这是一个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多神”的启蒙后时代,不再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普遍的元价值,不再有一个终极性的改革合法性标准。一切只有放在具体的问题语境之中,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和争辩,才有可能形成某种共识或互相理解。 不幸的是,当启蒙思想分化以后,在知识分子迫切需要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以形成各社会思想和实践合法性基础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却失去了公共性。 英国思想家鲍曼(Zgmunt Bauman)用两种隐喻来表达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功能。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是“立法者”,意思是说在现代社会整个知识一体化,没有完全分化。而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这套客观化知识,主要是一套客观的、中立的、程序性的陈述和规则。它在现代社会,拥有仲裁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只有程序性的规则才能保证获得客观的真理和有效的道德判断。因为这样的程序性规则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所以运用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也具有了普遍的有效性。因此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这套客观的知识,就能够超越其他阶层,成为知识的仲裁者。在鲍曼看来,在现代社会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其地位无可替代。借用布迪厄的说法,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福科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然而到后现代社会,鲍曼指出,由于整个社会开始多元化,使得整个知识系统也开始解体了,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整个社会的知识场被分解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彼此孤立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各自有各自的知识范式和知识传统,彼此之间甚至是不可通约的。鲍曼指出,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只有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才能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出共同体之外便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立法者”。这样,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变成一个“阐释者”。“阐释者”的角色就是将自己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翻译、阐释为其他共同体成员能够理解的知识。知识分子实际上不再具有“立法者”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性质,而仅仅只是一个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被扭曲的“阐释者”。鲍曼特别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是理性、真理等这样一些立法者所借以合法化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但到了后现代社会被共同体这一概念所替代。不同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分属不同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在最基本的价值上也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 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启蒙阵营的破裂,使得维系80年代“态度同一性”的整体元话语崩盘,由于知识背景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几乎在任何问题上,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形成共识,而会形成激烈的争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到21世纪初的时候归于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反而预示着问题的无法解决:80年代所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民间思想界,如今已经四分五裂,分化为各种知识问题、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信仰所形成的封建割据。这是90年代争论所遗留的重大后遗症。虽然分化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市场的标志之一,多元社会也以此为基础,但多元并不等同于离散,如何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的新的历史条下,重建对现代性的基本共识,并在思想界建构知识分子相互交往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公共知识传统,这不仅需要外部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性条件,而且也需要交往理性的行业规则、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和论辩伦理,这样的话,从90年代开始分化的各种思潮、流派和观念才不致走向极端,才有可能形成合理的多元平衡。从80年代到90年代,无论是启蒙者还是反启蒙者,都以启蒙的意识形态立法者自居,如今是如何从立法者转化为阐释者的时候了。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死去的是启蒙传统中各种绝对主义元话语,而永恒的将是启蒙思想中的交往理性和批判精神。
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摘自《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第二章:当代中国启蒙的内在紧张。许纪霖著。 改革在80年代就像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一样,属于神圣词汇,改革具有某种魔力,它承诺所有的社会阶层在改革之中都能获得利益,因而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改革打破了束缚人们多年的传统集权体制,资源集中在国家手里,赋予了全体人民相当的自由创造、发财致富的机会和权利。那时候的改革的核心是放权让利,是一场多边双赢的游戏。大家在改革中,所失去的只是锁链。如果说80年代改革的结果是多边双赢的话,那么90年代的改革就渐渐变化为一场零和游戏。这就发生了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围绕着改革的合法性,90年代发生了两场论战,一场是90年代初的激进与保守的论争,另一场是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前一场论争同样发生在启蒙阵营内部,其核心问题是改革的模式之争。80年代改革的合法性是以革命的名义论证的,改革就是革命,但到90年代,革命的神圣性被消解,引起了对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清算,谁该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失败负责?这样,革命就以激进主义的名义受到了审判,而保守主义又成为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得到了理论上的平反昭雪。激进与保守,背后所预设的,是墨子刻所说的转化与调适的两种对理性的认识论,分别以法国的唯理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为背景。激进与保守论战,最后以保守的大胜而结束,这也预示着自由主义即将脱下各种包装,浮出水面。 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一轮改革,这一轮改革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延续并加快了80年代以来的改革步伐,结果所形成的是从80年代就开始了而到90年代中后期明显定型的三大变化趋势。第一,从政治形态而言,从全能主义的政治转变为善治主义的政治。到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社会的基本确立,中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控制一切的全权主义集权政治,而改变为国家基本放弃了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控制而主控政治领域、在执政理念上照顾和体现民意的善治主义政治。按照康晓光借鉴金耀基提出的概念分析,这一善治主义的政治采取了一种“行政吸纳政治”的治理模式,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尊重和代表精英集团的利益从而获得精英们认同的基础上的。 第二,与此相适应,当代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则从一个总体主义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断裂的社会。按照孙立平的研究,1949年中国所建立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精英的位置不再存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从这一意义上说,总体性社会也是一个“无统治阶级的国家”。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推开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精英阶级。这些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和地方权力精英,虽然人数很少,却控制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成为强势利益集团。精英与一般的民众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资源占有以及与国家沟通能力上,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精英与大众的社会断裂层。这些断裂,不仅发生在精英与大众不同的阶层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同一个阶层内部。断裂,意味着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互相交往的整体,相反的,各个断裂层之间充满了忌恨和隔膜,缺乏最基本的公共信任,从而潜伏着冲突的危机。 第三,改革的游戏规则从打破旧体制的多边双到资源再分配的零和游戏。改革本来是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按照什么样的理念改革,改革对谁有利,成为90年代改革的突出问题。90年代在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精英利益集团,逐渐介入、控制甚至主导了改革的方向和方案,而政府本来应该是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调节者,但在地方政权一级,本身也利益化,与地方的强势精英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关系。而无法介入改革决策的民众,则成为改革的牺牲品。改革的游戏规则从80年代的多边双赢逐渐蜕变为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在所谓的市场竞争、适者生存的理念指导下,造成了一个赢者通吃的局面。一方面是极少数的所谓竞争得胜者,他们垄断了大部分的资源和成果,另一方面是绝大部分的失败者,他们只能得到改革后的残羹冷饭。正如秦晖所分析的,所谓的赢者通吃,在中国不平等的市场规则之中,实质就是权者通吃。 对于改革以来发生的上述变化,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有基本的共识,也对这一现状不满,也一致认为中国除了继续改革,没有任何出路。然而,这些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其根源在何处?又往什么方向改革?按照何种理念?何为改革的优先性原则?在这一系列涉及中国改革和现代性的最基本问题上,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一分歧突出表现在改革的合法性争论上:谁之改革?何种正当性?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就是改革合法性争论的表面化。这场90年代论争的压台戏,涉及范围之广、问题之深刻,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也罕见。这场大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在90年代资本与权力相互渗透和利益高度分化的背景下,什么样的改革具有合法性,因此形成了四个层面的重大分歧:第一是两种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歧,第二是两种民主(宪政民主与全面民主)的分歧,第三是两种公正(交易公正和分配公正)的分歧,最后是关于对现代性的理解上的分歧。而在这些分歧的背后,又涉及80年代启蒙运动中本来已经自明的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民主等一系列基本范畴的重新评价和历史分析,以及对9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这场论战对90年代具有总结的性质,因其在时间上跨世纪,因而对21世纪的中国继续发生着重大影响。 自这场大论战之后,国内外的舆论出现了一种将中国思想界分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大阵营的简单二分法,并权且按照这一二分法为众多知识分子重新站队。应该说,这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二元法是一种具有相当误导性的化约主义,它将中国知识分子对改革的分歧,化约为两种非黑即白的思想倾向。事实上,在当代中国,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其内部都有着相当复杂的区别,特别是在被称为自由主义的阵营中,既有在政治上相当保守而在市场上非常激进的发展至上的经济自由主义,也有注重宪政改革和个人权利的政治自由主义,还有兼顾自由与平等的左翼的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以及其内部的分化,随着论战的深入,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到9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所呈现的,不是对比强烈的两极图景,而是远为丰富而复杂的思想光谱。 如果我们不是分得更细的话,可以说当代中国思想界在改革的问题上,已经分化为五种政治思潮:发展主义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左翼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 发展主义的代表者主要是一批目前在中国经济学界名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渊源主要是里德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发展主义相信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应该来源于企业的制度创新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要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推动产权的私有化改革,解决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发展主义以发展至上为中心,将中国改革定位在企业创新、私有化改革和落实私有产权的合法化这几项经济目标上,至于社会的分配不平等问题,他们认为这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可以等到经济发展以后再来解决。至于政治的自由和民主问题,也被发展主义的发展至上的理念暂时搁置在一边。发展主义到90年代已经体制化,成为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且明显地代表了经济精英的利益和诉求。 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者是一批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坚定的反对者,他们奉哈耶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为自己的理论圭臬,相信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和宪政民主制度,而其前提就是要在法治框架之内,落实包括人身、财产、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内的最基本的人权。他们虽然与发展主义一样赞成私有化,但认为目前的私有化是不公正的,而社会不平等的症结,在于权力远远没有退出市场,是“看得见的脚”干扰了“看不见的手”,唯一解决的途径是全面彻底的市场化,切实落实私人的财产权,将权力完全逐出市场,以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在政治领域,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者坚信,中国目前所有问题,包括腐败和市场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因为政治上缺乏民主宪政和现代法治,特别是缺乏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他们呼吁要在政治改革上着手,全面落实和保障个人的“消极自由”。 新左派是从80年代启蒙运动分离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在国外留过学,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影响。他们将上述的发展主义和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统称为“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为全球资本主义中国化辩护的意识形态。新左派强烈批评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资源再分配中,少数权贵成为最大的得益者,而广大平民成为被剥夺的牺牲品。他们认为这一分配极其不公的国有资产掠夺过程,正是打着“自由经济”、“私有产权”的旗号进行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替少数权贵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提供合法性的借口而已新左派进而指出,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历史中也是一个虚幻的神话,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操控和垄断市场。市场中所谓的机会平等遮蔽了实质的不平等。要实现社会的公正,唯有落实社会经济的民主,让底层民众能够参与经济生活的决策和管理,并在资源分配上向弱势群体倾斜。新左派虽然不反对政治改革,但他们不满意“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消极自由”和“间接民主”,追问是谁之“自由”,何种“民主”。他们批评说,这些表面平等的“消极自由”只是少数权贵能够享受的“自由”,而与广大民众无涉。他们要进一步落实能够保障一般平民广泛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并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保证广大平民享受普遍的生存权和福利权,真正落实自由与民主的基本条件。 左翼自由主义是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他们虽然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与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对新左派虽然有批评,也有部分的同情性了解。在他们看来,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太“右”,而新左派太“左”,对于中国来说,需要超越“左”与“右”的两极,探求一条兼顾自由与公正的“第三条道路”。而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这些欧美的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左翼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他们认为,在中国,不仅需要落实个人的自由,也需要解决社会的公正。他们不像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那样迷信市场,而是认为有好的市场,也会有坏的市场——即权贵资本主义垄断下的市场。在这一被权力扭曲的市场中,哈耶克式的交易公正是不够的,也是很难实现的,必须还有分配的公正,通过国家的制度化力量,在不违背自由的优先性原则之下,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而在政治上,在赞成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同时,又提出公民共和主义和商议性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作为补充,在选举民主之外重视公民文化公民参与和公共领域的公共讨论。 新保守主义思潮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经以新权威主义的形式出现,到90年代中期以后,其善治主义的威权政治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并且也内化到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使得新权威主义不再是一种独立的、有影响的改革思潮。不过,90年代所出现的上述政治模式、社会结构和改革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重提保守主义,这一新的保守主义旨在调和国家、精英和民众的紧张关系,克服出现的社会断裂危机,以建立一个合作主义的国家模式。简单地说,这一合作主义的政治模式,有四项要求:第一,统治集团必须约束自己的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即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权威主义政府;第二,限制经济精英的非法利益,同时完善法治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但要坚决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第三,扩大知识阶级的权利,特别是要保证他们的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第四,保护大众的基本权利,建立法团主义体制和福利国家。 上述这五种改革的思潮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有着或者直接,或者曲折的利益背景,但作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理念,它们更多地体现了超越利益之上的“真理宣称”( truth claims)。承继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知识分子总是将自己看作中国改革的立法者,相信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真理宣称”。而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是异常复杂的,启蒙思想的内在传统也是多元的。启蒙思想内含的众多的价值理念—发展、进步、自由、平等、法治等等,一旦遭遇到复杂的改革处境,就需要启蒙知识分子作出价值性选择:何为自己所理解的最优先的改革原则。而继承了不同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也就在90年代这样一个启蒙后时代里面,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对改革之合法性的论证因而也具有了各有其价值秉承的多元阐释。这是一个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多神”的启蒙后时代,不再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普遍的元价值,不再有一个终极性的改革合法性标准。一切只有放在具体的问题语境之中,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和争辩,才有可能形成某种共识或互相理解。 不幸的是,当启蒙思想分化以后,在知识分子迫切需要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以形成各社会思想和实践合法性基础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却失去了公共性。 英国思想家鲍曼(Zgmunt Bauman)用两种隐喻来表达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功能。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是“立法者”,意思是说在现代社会整个知识一体化,没有完全分化。而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这套客观化知识,主要是一套客观的、中立的、程序性的陈述和规则。它在现代社会,拥有仲裁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只有程序性的规则才能保证获得客观的真理和有效的道德判断。因为这样的程序性规则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所以运用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也具有了普遍的有效性。因此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这套客观的知识,就能够超越其他阶层,成为知识的仲裁者。在鲍曼看来,在现代社会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其地位无可替代。借用布迪厄的说法,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福科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然而到后现代社会,鲍曼指出,由于整个社会开始多元化,使得整个知识系统也开始解体了,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整个社会的知识场被分解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彼此孤立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各自有各自的知识范式和知识传统,彼此之间甚至是不可通约的。鲍曼指出,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只有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才能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出共同体之外便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立法者”。这样,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变成一个“阐释者”。“阐释者”的角色就是将自己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翻译、阐释为其他共同体成员能够理解的知识。知识分子实际上不再具有“立法者”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性质,而仅仅只是一个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被扭曲的“阐释者”。鲍曼特别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是理性、真理等这样一些立法者所借以合法化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但到了后现代社会被共同体这一概念所替代。不同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分属不同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在最基本的价值上也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 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启蒙阵营的破裂,使得维系80年代“态度同一性”的整体元话语崩盘,由于知识背景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几乎在任何问题上,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形成共识,而会形成激烈的争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到21世纪初的时候归于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反而预示着问题的无法解决:80年代所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民间思想界,如今已经四分五裂,分化为各种知识问题、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信仰所形成的封建割据。这是90年代争论所遗留的重大后遗症。虽然分化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市场的标志之一,多元社会也以此为基础,但多元并不等同于离散,如何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的新的历史条下,重建对现代性的基本共识,并在思想界建构知识分子相互交往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公共知识传统,这不仅需要外部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性条件,而且也需要交往理性的行业规则、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和论辩伦理,这样的话,从90年代开始分化的各种思潮、流派和观念才不致走向极端,才有可能形成合理的多元平衡。从80年代到90年代,无论是启蒙者还是反启蒙者,都以启蒙的意识形态立法者自居,如今是如何从立法者转化为阐释者的时候了。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死去的是启蒙传统中各种绝对主义元话语,而永恒的将是启蒙思想中的交往理性和批判精神。

